今年飞絮比去年稍晚了一些。刚想感叹去年园林绿化局给30万棵雌株杨树打的「抑花一号」效果显著——这种药剂可以形象地理解为「避孕药」,能让雌株杨树只长叶子不开花,次年生效——没多久,北京气温一上来,飞絮又一次围剿北京城。
现在北京五环内一共有28.4万棵杨柳雌株,这是园林绿化局截止到2018年底的数据,其中朝阳区的杨柳雌株最多,有10.7万株。这些杨柳雌株已经被精准定位,还形成了数据库。官方说法是,到明年,杨柳飞絮就可以明显改善。
无论如何, 春日短暂,还是戴个口罩上街吧。
1
北京4932条街道里散落着200万棵雌株杨柳树。雄株杨柳树不飘絮,但北京超过60%的杨柳树是雌株,而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毛白杨的杨絮就足够铺满一条街。杨絮先到,柳絮一个星期后跟上,只要春日里连续3天最高气温超过25℃,整个北京城就会如同被扔进毛球修剪器挤满白色毛屑的收集盒里。
记者查非是重度粉尘过敏患者。她每天生活在「无菌房」中,扫地机器人一天打扫两次,空气净化器24小时开着,两台吸尘器一个随时吸角落另一个吸床铺沙发。但一到杨柳絮飘飞的4月,她会变得格外惶恐,不管再怎么小心翼翼,那些被吹进楼道、聚在门口的杨柳絮总会在她开门收快递、取外卖的一瞬间冲进家门。
几位大学生鼻炎患者对杨柳飞絮发起了挑战。他们把生化实验室里使用的护目镜戴出室外,像在海里潜水一样,在飘絮的路上无障碍行走。
飞絮也不善待非过敏患者。一位每天出门遛弯的大爷形容走在飞絮密集的路上「等于被打脸」。在微博用户Hsuan_Li的描述中,「春天的北京就像一场集体葬礼,出门走两步感觉就被埋了。」在眨眼、呼吸、说话之间,这些纤维长度只有5毫米的绒毛都有可能钻进五官。为了揉出飞进眼睛里的飘絮,有人把隐形眼镜揉了出来。有人打个哈欠吃进了飞絮,还产生了奇异的饱腹感。还有人喝了半瓶醋试图降解窜进嘴里的飞絮,却一时难以缓解喉咙里黏糊糊的感觉。
在飘絮时节进行户外运动更是一项艰巨的考验。前年4月的一场高尔夫公开赛上,绵延的草坪上方密集地飘荡着飞絮。戴着口罩的观众在一旁伸长脖子观看没有戴口罩的选手们挥杆,在白色绒毛的环绕下,高尔夫球被击向远处,但不清楚球飞到何处。
10年前,北京春日的飞絮就已显著。2008年国际射联世界杯在户外举办男子飞碟双多向赛时,喷水车在飘絮的靶场上不停洒水以盼能凝住这些麻烦的绒毛。俄罗斯选手瓦西里·默森端着枪集中精力看靶,柳絮却在四周飞来飞去。打完一发子弹的喘息瞬间,他还得小心别误吸柳絮。这位最终获得金牌的老将赛后委婉表达了自己遭受的困扰,「这些『雪球』增加了我获胜的难度。」
在栽种了近10万棵杨树的机场高速路的附近街区上,一位摆摊摊煎饼的大爷见惯了每年春天的飞絮,但他坚决否认了煎饼飞进飘絮的可能。一位28岁的男士咨询医生,在路边摊吃饭,柳絮飘进碗里,吃下去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医生劝他不必担心,除非过敏,柳絮对人一般没有危害,「相比于柳絮来说,建议你还是能少在路边地摊上吃,可能这对身体的危害更大。」
一部分户外工作者没有在飞絮天里戴口罩的权利。一位在北京工作了16年、穿着洗得发白的绿色制服治安巡逻员,回到家一洗鼻子,鼻腔里都是黑的。这份职业要求他保持形象,不准戴口罩,「领导的话你得听啊,不听话你可以走。」
在飞絮中摆过摊的一位大妈则热衷于传播从网上看来的杨柳絮段子:一位记者采访清理杨柳絮的环卫工人,「大妈,柳絮对你带来什么影响?」环卫工人回答,「影响可大了,首先你看清楚我是你大爷!」
飞絮对道路交通的干扰也相当棘手。一位中年男司机因为开车时无意飞进车内的飘絮而连打喷嚏,在沪宁高速连接线处开出了「S」路线,被交警误以为是酒驾并拦停。一位十几年驾龄的出租车司机在载客去解放军309部队医院的路上,因为太多飞絮通过车前的风道糊在发动机水箱的散热器上,车开到半路,水箱里的水沸腾了。
和人一样,马也承受着来自飞絮的困扰。也许更糟糕,它们只能通过频繁地打喷嚏这个动作来表达不适。在北京一家马术俱乐部,打喷嚏前马会点点头,眼神闪烁,随后飞絮混杂着其他鼻腔异物被一并喷出。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PM2.5监测仪对杨柳飞絮同样无可奈何。每年四五月飞絮时,监测数据曲线会突然升高——监测设备采样头没有杨柳絮过滤机制,杨柳絮容易被吸入或堵塞采样头——持续1-2个小时又迅速回落,和医院里的心电图一样让人心惊。
五道口一位不习惯戴口罩、声称飘絮时咳出的痰比平时要黄的大厦保安,不仅要仔细观察大厦四周有没有小偷小摸的行人,在飞絮季节里还需承担更加重要的踩烟头任务——一根没熄灭的烟头可以达到800摄氏度,而10平米的飞絮遇到明火能在2秒内烧完。
去年5月1日,北京119指挥中心接到了377起以杨柳絮火灾为主的报警。蟹岛度假村的停车场当天因为飞絮堆积,被烧毁了近90辆车,其中20多辆大巴车直接被烧成空壳。这场持续了3小时的大火最终被50辆消防车扑灭。引燃飞絮的源头至今不明,有传言是一根没熄灭的烟头。
突如其来的好奇心是多场火灾的导火索。「就是人为因素,玩火的,好奇为主。」朝阳区公安消防支队宣传中心主任杨敬博说。有位时尚杂志编辑为了给燃烧的飞絮拍照,烧损了2个路灯灯罩、3辆汽车、612棵树,被追偿了50多万元。
一位58岁的男士在路过小区自行车棚时,看到路面堆积的大团柳絮,抱着重温童年时玩儿的心态,一边抽烟一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把地上两团柳絮点燃。没等柳絮烧完,他转身刚走10分钟,车棚燃起大火,冒出黑烟。十几分钟后他折返回来,慌张地扛着灭火器灭火,但火势早已超出了他能控制的范围,十几辆自行车和一辆比亚迪被烧毁。他被刑事拘留。
2
北京春日短暂,零星的绿点儿总是很快地蔓延到绦柳、毛白杨、国槐、银杏、刺槐、悬铃木,枝桠像羽毛一样在道路两边伸展开,绿叶子摇摇摆摆。绿色小辣椒串一样的雌花在笔直挺拔、几十米高的雌株毛白杨树上裂开,一点一团的白色杨絮随风飘上街,春天在北京才正式掀开。
北京第一批杨絮来自1970年代之后种下的河北易县雌株毛白杨,这是流行于园林界的说法——但有关杨絮的考古研究是相当混乱的,另一位园林学家不能确认最早的源头,但他斩钉截铁地认为,1970年代的毛白杨大多是雄株,目前城区的易县雌株,从粗度看最多是1990年代以后栽植的。
如果前一种更为有据可考的说法向后推演,这种雌株当年在钻天杨、加拿大杨、北京杨、欧美杨、毛白杨等「百杨齐发」的年代,因为价格便宜、易活、生长快而作为优秀品种被挑选出来,前往植物覆盖率只有20%、1977年被列为「世界沙漠化边缘城市」的北京。
至于雌株此后对城市带来的影响,在种树时还少有人预料。但很快,治理飞絮问题从1980年代就提上日程。一位当年的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曾尴尬地表示,「当年确实没注意性别问题。」
为了对抗漫天飘絮,极具首都特色、声势浩大的「百万雄杨进北京」工程在1990年代中期提出。这批雄株毛白杨迅速占领北京的多条道路。但相比之下,这批雄杨远不如易县雌株生命力顽强——从种下后第3年开始,这批号称抗病虫害的雄杨超过30%患上溃疡病,或受到桑天牛的侵扰。
百万雄杨的结局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这个浩大工程对治理杨柳絮没多大帮助。2001年,北京超过50%的杨树仍是雌株。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飞絮已经造成了「恼人」的困扰。这一年,首都绿化规划中明确规定,雌株毛白杨不可以再作为北京绿化的主要树种。
明令规定并没能遏制住雌株杨树的扩散。21世纪初,为迎接08奥运,北京进行了城市改造和道路扩建,四环路、五环路、机场路两旁相继出现了一片片的雌株杨树。一位了解内情的园林专家告诉《人物》记者,「虽然北京市都要求栽雄的,但是这些苗圃企业在给苗子的时候,实际拿出大多数都是雌的。」
性别问题让树苗购买方相当头疼。雌雄杨柳树在「未成年」之前难以通过肉眼辨别雄雌,要么把树苗送到专业实验室做DNA图谱检测,要么信任了解树苗来源的苗圃的说法。大多雌株杨树比雄株生长速度快,有苗圃用雌株替代雄株销售出去,等七八年后突然开花飘絮购买方才意识到受骗,但「那时候苗圃可能都没了」。
2004年,北京一条两侧种着高大雄株毛白杨的道路为了扩建,砍掉了其中一侧的雄株毛白杨,道路修建完,新的一侧却种上了雌株毛白杨。14年过去,那位园林专家打车经过这条路,道路两边的毛白杨一边粗一边细,一边飘絮一边不飘絮,「对比非常强烈。」
没有人宣布对此路负责——当被询问这条路具体的规划方,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处得到的回答是,「可能是林业局,也可能是路政或区园林绿化局,我们只负责制定总则,具体实施不清楚。」
3
为了治理飞絮,北京曾在5年内减少了180万棵杨柳树。
杨柳树有极大的生态效益,一株胸径20厘米的杨树一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72公斤,释放氧气125公斤,滞尘16公斤。同样大小的柳树,一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281公斤,释放氧气204公斤,滞尘36公斤。
它们也是北京人的老朋友,一直以来都是北京绿化的主力树种。柳树最早发芽、最晚落叶,北京「有水的地方就有柳」,垂顺的绿枝条是这座北方城市柔软的一部分。
笔直挺拔、二三十米高的杨树在道路宽阔的北京是另一种象征般的存在,茅盾在70多年前就形容它是「力争上游」、压迫中保持倔强挺立的树,像被加工过一样,「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就连宽大的叶子也「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
高大的杨树是北京记忆的一部分。赵忠祥在回忆录里写道:「杨树在北京真是多得不得了……几年工夫一株杨树苗就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漂亮的树冠,肥硕油绿的树叶子,迎风哗哗作响,雨中亦闪闪发亮,秋后树叶飘零,随风满地落叶乱走。」
但人们同时也饱受困扰。北京开始了一系列无法根治飞絮的措施。
花2年时间研制出的杨树雌花序疏除剂如同「堕胎药」,其机制是等开花但还没飘出絮时,用化学药剂把花打掉。要准确掌握杨树雌花序长到4-6cm的时机喷洒,要准确掌握喷洒药剂的力度和方向,太多太少,偏左偏右,都会有二次污染——要准确的事儿太多,城市不是实验室,科学家也办不来。
北京奥运会前,总数一度超过900万株的柳树里,有80%都是雌株,春天里全是失控的柳絮。一位江苏的园林学家从央视新闻得知北京制定了几次计划砍伐柳树,他赶紧建议留下北京的雌株柳树,为它们高位嫁接雄性枝条。
柳荫公园里的45棵雌株柳树获得了第一次体验「变性手术」的机会——柳树的性别取决于枝条。2005年3月,它们的枝条被全部剪除,留下像电线杆一样的主干,树顶上裹着一圈白布,几根不到30厘米长、来自南方不飞絮的金丝垂柳的枝条倒插在树顶上。3个月后,嫁接的柳树长出了1米多长的枝条。但一棵「术后」光秃秃的树干上飘着几枝柳条的柳树要恢复成自然、茂盛的状态,需要3年。
10年里,全北京只有1000棵雌株柳树获得了珍贵的改变「性别」的机会。嫁接的技术要求高,维护成本也高,为了防止「性别」反弹,需要有人不断去除树干上不时冒出的雌株新芽。
2007年,一款专属于雌株杨柳树的「避孕药」——「抑花一号」被包括32岁的车少臣在内的3位园林学家在不到1年时间里研制出来,这种从20多种药剂复配筛选出的药剂能让雌株杨树只长叶子不开花。
如何让雌株杨柳树顺利服下这个药剂,是他们研究的难点。他们没有选择常见的「吊袋输液」的树干注射技术,改用了高压注射技术,从「打吊针」变成「打针」。车少臣想象一棵树吊三五个袋子,再随风一飘,「我的天,这个观赏效果实在是有点无法忍受,给人的感受就是这个树病得不得了了,病入膏肓。」
2017年,北京有40万棵雌株杨柳树体验了这一计生措施。「服药」的正确方式是,用电动打孔机在树干上每25厘米处打一个直径1厘米、深度3公分的洞,再用高压注射仪器往洞里注射调配好的药剂。这是一份需要耐心、细心、又讲究经验的工作,一旦把雄株错认为雌株,让人心疼的不仅是被多打了几个洞的雄株,还有浪费了的药剂——一瓶25g的「抑花一号」就要百来元。
然而这也不是一种完美的方案,药每年都要打,叠加的成本不低。
直到2015年,「抑花一号」才畅销全国,这一年,国家林业局首次以「1号文件」的方式下发《关于做好杨柳飞絮治理工作的通知》。车少臣开始到全国各地出差,为大家讲解如何正确、安全地使用「抑花一号」。在此之前,「抑花一号」一直处在「费这么大劲但未来这些树还得换掉」的质疑之中。车少臣的专业是植物保护,他只想先把雌株杨柳树保护起来,不要因为飞絮就把它砍了。
事实是,杨柳已经不再是被这座城市欢迎的树木,另一位园林学家近几年来感受到的氛围是「全面禁养,不管雄的、雌的,实际现在就是基本不栽杨树」。
去年蟹岛大火第二天,北京城掀起了对杨柳飞絮的大清理。上到消防部门、园林部门、环卫部门,下到各公园、各街道办事处、各社区物业、各村居委会,人人惊恐地盯住这些在水泥城市里随风而动的白色絮状物。
每天至少在早晚两个时间段里,消防队会开着巡逻车寻找堆积的杨柳飞絮,向这些短暂停驻的絮状物上洒水。仅5月2日至3日,北京就出动消防车413部、洒水车305部、人员2950人,共洒水8750吨,湿化面积156.2万平方米。
北京五环内六个区里的30万棵雌雄杨柳树被追踪定位。以500米×500米为一单位,海淀、朝阳、东城、西城、大兴、丰台被划分成2866张A3大小的地图。350名多名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骑着共享单车对每500平米里的每一棵雌株杨柳树进行地毯式搜索。只要发现一棵雌株,他们就会为它在地图上标记一个点,并用锤子、钉子把一块银色的毽子底一般大小的穿孔圆铁片钉在树上,便于以后进一步治理。
有一户要从1米窄的胡同走进去的市民家,厕所里长出一棵雌株杨树,春天飘的絮紧实地堵住了他家纱窗上的每个小眼,量够塞成一个枕头。三年前,一位奥运冠军觉得杨絮和杨树的病虫害太烦,把小区里靠近自己家窗户的8棵雌株杨树的所有枝叶和1/3树干砍掉了,只剩下不到10米高、光秃秃的树干。被邻居举报后,城管介入调查,认为这是对「树木的修剪行为,没有违反规定,所以不予追究」。
杨柳树在北京逐渐失去了以往绝对的主导地位,国槐、银杏、椿树、白蜡在取代它们。
但看起来似乎总是很难找到一种完美的树。一位园林学家预言了国槐的未来——散生树种槐树一旦密植,必然产生虫害,使用杀虫剂就会带来污染,气候稍微一旱槐树就落叶落花落果,车辆碾过,制造出的粉尘可能比飞絮还严重。
为了4年后的冬奥会,北京决定「增彩延绿」。这一举措意味着属于这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城市的冬天,不再由萧瑟、灰白、肃穆来定义。
也许过不了多久,曾让一位1990年代来北京上大学的园林学家痴迷的高大挺拔的毛白杨将远离下一代人的记忆。白杨将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让人恍惚间分不清南北方的常绿植物和五颜六色的外来引进植物,它们决定这座城市未来的模样,也包括所有可见不可见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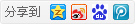
 添加到百度搜藏
添加到百度搜藏